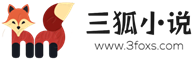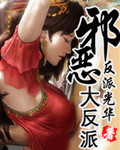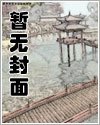第160章 刘采春:市井里的文化灯塔与柔情
一秒记住【三狐小说】 www.3foxs.com,更新快,无弹窗!
第160章刘采春:市井里的文化灯塔与柔情(第1/2页)
中唐苏州的玄妙观前,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——最前面的蹲在地上,中间的踮着脚尖,后面的爬到旁边的菜摊上,都为看“采春班”的演出。
刘采春一开口,连卖糖葫芦的都忘了吆喝,连赶驴车的都停了脚——她的戏,不只是逗乐解闷,更像一面镜子,照出了当时老百姓的日子;她的歌,也不只是流行小调,而是扎进民间文化里的根,连千年后的我们,都能顺着这根,摸到大唐市井的烟火气。
而舞台背后的她,卸下戏服,也是个会疼女儿、会跟丈夫拌嘴的普通女人,把柔情藏在赶路的驴车里、缝补的戏服上。
民间生活的“活史书”,后世通俗艺术的“引路人”
正史是给帝王将相写的“精装书”,那刘采春的《啰唝曲》和表演,就是给老百姓写的“家常日记”——里面记的不是宫廷政变、边疆战事,是商人媳妇的眼泪、码头的等待、过日子的苦与盼,这些细碎的日常,偏偏是正史里最缺的,也是最能让我们读懂“中唐老百姓怎么活”的关键。
照见中唐民间的“真日子”:商人多了,分离也多了
中唐跟盛唐不一样了——盛唐时大家都盯着长安的皇宫,中唐时江南的商船多了,“经商”不再是丢人的事,好多男人放下锄头,驾着船去扬州、广州做买卖。男人走了,家里的媳妇怎么办?正史里写“商旅益盛”,却没写这些媳妇怎么过日子;文人诗里写“闺怨”,却没写她们会拿金钗卜卦、会在码头错认船。刘采春却把这些都唱了出来。
听《啰唝曲》里的“莫作商人妇,金钗当卜钱”——不是她瞎编,是她跑江湖时真见得多了。在杭州的码头,她见过王婶把陪嫁的银镯子当卜具,扔一次哭一次;在绍兴的市集,她见过李嫂每天天不亮就去江边,看见挂“广州”旗子的船就跑过去,结果每次都空着手回来。这些场景,正史里不会记,刘采春的词记了,成了最生动的“社会档案”。
有次越州刺史元稹跟她聊天,说:“我看你的词,比我读的《郡国志》还懂江南。”刘采春笑着说:“大人读的是州府的事,我唱的是老百姓的事——他们的日子,都在码头、在灶台、在等男人的眼泪里呢。”
确实,从她的词里,可以摸清中唐民间的“脉搏”:比如“桐庐人不见,今得广州书”,说明商人做生意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,会从桐庐跑到广州,路途远、归期不定;比如“黄河清有日,白发黑无缘”,说明当时女人都怕等丈夫等老了,怕“他回来时,我已经认不出了”。这些细节,让我们知道,中唐的“繁华”不只是扬州的盐商、苏州的丝绸,还有背后无数个等待的家庭——刘采春把这些“不显眼的繁华”唱了出来,让大唐不再只有帝王的辉煌,还有老百姓的活色生香。
给后世通俗艺术“搭梯子”:大白话也能成好作品
刘采春最了不起的,不是唱红了几首词,是她让“通俗”成了一种能传下去的艺术风格——以前文人总觉得“大白话登不了台面”,写诗得用典故、讲对仗,可刘采春偏不,她用“不喜秦淮水”“错认几人船”这种老百姓嘴边的话,照样能把人唱哭。后来的民间艺术,好多都踩着她搭的“梯子”往上走。
看元代的散曲,关汉卿写《窦娥冤》,窦娥哭爹时唱“爹爹,你直恁的信口胡言!”,多直白?跟刘采春的“莫作商人妇”一个路子,不绕弯子,有啥说啥。还有明清的民歌,比如《挂枝儿》里的“想郎想得肝肠断,泪湿了红绣衫”,跟《啰唝曲》的“朝朝江口望,错认几人船”,都是用最朴素的话写最真的情,没有半分矫揉造作。
就连现在江南还在唱的《茉莉花》,“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,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”,语言通俗,旋律婉转,跟刘采春唱《啰唝曲》的路子也像——都是老百姓爱听、爱唱,能随口哼出来的。有个研究民间音乐的老先生说:“刘采春是把‘民间话’变成‘艺术话’的第一人,没有她,后世的民间小调可能还在‘模仿文人诗’,找不到自己的路子。”
她的表演风格也影响了后来的戏曲。以前的“参军戏”多是男人演,刘采春加了女人的视角,还把“唱”和“演”揉得更紧——她唱“金钗当卜钱”时,会真的做“扔金钗”的动作;唱“错认几人船”时,会真的“踮脚望”。后来的越剧、黄梅戏,好多旦角表演“思夫”,都会学她的样子:比如《天仙配》里七仙女等董永,会站在门口“朝朝望”,眼神里的盼与失落,跟刘采春当年的表演,隔着千年都能看出传承。
刘采春就像民间文化的“灯塔”——她没在皇宫里演过,没被皇帝夸过,可她的光,照在市集的戏台、码头的石阶、老百姓的院子里,让通俗的、来自生活的艺术,也能活得有底气、传得远。
后台的柔情——驴车里的家,戏服里的暖
舞台上的刘采春,是能让观众哭、让观众笑的“角儿”;一卸了戏服,她就是周季崇的媳妇、周德华的娘、周季南的嫂子,会累、会烦、会心疼人,把柔情藏在最普通的日常里。
家庭戏班:不是伙伴,是“拆不散的一家人”
“采春班”从来不是“刘采春一个人的戏班”——是丈夫周季崇打板、兄弟周季南逗哏、女儿周德华伴舞,连赶驴车的老周(周季崇的远房叔),都算半个家人。他们的日子,一半在戏台,一半在赶路的驴车上。
有次去常州演出,半路遇上大雨,驴车陷在泥里,轮子转不动。周季崇和周季南挽着裤腿在前面推,刘采春抱着刚满五岁的德华在后面扶,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流,打湿了戏服。德华冻得哭,喊着“娘,我冷”,刘采春就把外衫脱下来裹在女儿身上,仅穿件单衣,还笑着说:“咱德华是小英雄,再忍忍,到了常州娘给你买糖糕。”老周在旁边赶驴,也跟着哄:“德华乖,驴儿也在使劲呢,咱们很快就到!”
(本章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)第160章刘采春:市井里的文化灯塔与柔情(第2/2页)
好不容易到了常州,找了家小客栈,刘采春先给德华洗热水澡,又给丈夫和兄弟煮姜汤,自己却顾不上喝,坐在油灯下缝补被泥刮破的戏服——周季崇的板带断了,她用粗线缝了又缝;周季南的帽子丢了个绒球,她就拆了自己帕子上的花,缝在帽子上。周季崇看着她熬红的眼睛,递过一杯热茶:“歇会儿吧,明天再缝也不迟。”刘采春摇摇头:“明天要演出,戏服破了不好看,老百姓花钱来看,咱不能糊弄。”
演出时,他们也总互相“救场”。有次刘采春唱《啰唝曲》,唱到“朝朝江口望”时,忘词了,脸一下子红了。台下有人开始起哄,周季南赶紧凑上来,扮成“苍鹘”(参军戏里的逗乐角色),故意摔了个趔趄,逗得观众笑,趁这功夫小声跟刘采春说:“错认几人船!”刘采春赶紧接下去,演出才没出岔子。下台后,刘采春有点不好意思,周季南笑着说:“嗨,谁还没忘过词?下次我先逗乐,给你留时间想!”
这种互相扶持,不是演出来的,是一路走出来的。他们没赚过大钱,驴车换了三辆,戏服补了又补,可没人说过“散伙”。周季崇常跟人说:“我家采春是台柱子,可没我们这几个‘搭子’,她一个人也唱不成戏。”刘采春也说:“要是没他们,我早撑不下去了——赶路的苦、演出的累,有家人在,就不觉得难了。”
她的情:把自己的思念,唱进《啰唝曲》里
刘采春唱的“思妇情”,不是瞎编的,是她也尝过“分离的苦”。有次戏班要去广州演出,路途远,德华年纪小,经不起折腾,留在苏州的亲戚家。走的那天,德华抱着刘采春的腿哭:“娘,你早点回来,我等你给我扎小辫。”刘采春蹲下来,给女儿擦眼泪,也红了眼:“娘很快就回来,你要听姨婆的话。”
一路上,刘采春总想起女儿——赶驴车时,看见路边的小丫头,就想起德华扎着双丫髻的样子;吃饭时,看见别人的孩子吃糖,就想起德华爱吃的麦芽糖。到了广州,她第一次唱《啰唝曲》里的“昨日胜今日,今年老去年”,就想起女儿:自己出来这几天,德华会不会想娘?会不会长高一点?唱到“白发黑无缘”时,声音忍不住抖了——她怕自己在外演出,错过女儿长大的日子,怕女儿认不出自己。
台下有个广州的媳妇,听她唱得动情,递上一块帕子:“姑娘,你是不是也想家里人了?我家那口子去扬州,我也总这样想。”刘采春接过帕子,擦了擦眼睛,点点头:“我女儿在苏州,我出来好几天了,想她。”那天演出结束后,她第一次给家里写了信,信里没说演出多热闹,写“广州的花很好,等我回去,给德华带一朵”。
后来她唱《啰唝曲》,总带着点自己的思念——唱“金钗当卜钱”,就想起临走时,德华把她的小银钗塞给她,说“娘,这个能保佑你早点回来”;唱“朝朝江口望”,就想起在广州的码头,盼着寄给家里的信能早点送到。这种“把自己放进去”的深情,让她的词不只是“唱别人的故事”,更像“跟观众说自己的心里话”,所以才那么打动人。
有次周季崇跟她说:“你唱《啰唝曲》时,眼里有光,也有泪。”刘采春笑着说:“因为我知道,等的苦是什么滋味——我盼女儿,她们盼丈夫,都是一样的。”
大唐市井里的“真艺人”,千年不褪色的“柔情”
刘采春这辈子,没进过皇宫,没当过官,甚至没留下一张画像,可她比好多文人都活得“鲜活”——她的《啰唝曲》,不是写在纸上的死文字,是能唱、能演、能让老百姓哭的活情感;她的家庭戏班,不是冷冰冰的“演出团体”,是能一起推驴车、一起缝戏服、一起扛苦日子的一家人。
她的文化影响,不是靠皇帝的赏赐、文人的吹捧,是靠老百姓的“口口相传”——苏州的媳妇教女儿唱《啰唝曲》,杭州的戏班学她的表演,后世的民间艺人跟着她用“大白话写真情”。她就像民间文化里的一颗“种子”,落在大唐的市井里,长出了后世通俗艺术的枝丫。
而她的柔情,也不是舞台上的“表演”,是后台驴车里的姜汤、缝补戏服的粗线、想女儿时的眼泪——这些最普通的日常,让我们知道,再厉害的“角儿”,也是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,也会疼、会盼、会牵挂。
再读《啰唝曲》,不会只觉得“这是一首思妇诗”,会想起中唐苏州的码头,想起刘采春抱着女儿赶驴车的样子,想起那些在江边等船的媳妇——她们的苦与盼,通过刘采春的歌,穿越了千年,还能让我们觉得“这说的是我身边的事”。
刘采春没留下什么贵重的遗产,她留下了最珍贵的东西——大唐市井的烟火气,和老百姓最真的深情。这种深情,不会因为时代变了就褪色,就像她唱的“不喜秦淮水,生憎江上船”,不管过多少年,还有人在等、有人在盼,就会有人懂这句词里的滋味。她,就是大唐民间最活色生香的“真艺人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