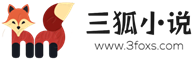第159章 刘采春的艺术:大白话藏着真眼泪
一秒记住【三狐小说】 www.3foxs.com,更新快,无弹窗!
第159章刘采春的艺术:大白话藏着真眼泪(第1/2页)
中唐的江南市集上,若有人问“为啥刘采春的戏能让卖菜的大妈放下秤、织布的姑娘停下梭子”,十个观众里有九个会说:“她唱的是咱们的心里话啊!”——不像那些文人写诗,满纸“之乎者也”,听半天摸不着头脑;刘采春不一样,她的词像街坊唠嗑,直白得很,唠着唠着,就能把人唠哭。这就是她最厉害的本事:把“通俗”和“深情”揉得恰到好处,让老百姓听得懂、听得进,还能记一辈子。
通俗:不说文绉绉的话,只讲老百姓的家常
刘采春最不喜欢的,就是“掉书袋”。那些文人写闺怨诗,爱用“青鸟”“鸿雁”当信使,用“梧桐”“芭蕉”表哀愁,老百姓哪懂这些?比如有个文人写“鸿雁不传书,梧桐更兼细雨”,卖鱼的大叔听了准得问:“鸿雁是啥?能吃吗?”可刘采春写思念,从不搞这些虚的,她只写老百姓天天见的、天天经历的事。
就说《啰唝曲》里的“不喜秦淮水,生憎江上船”——秦淮水是江南人天天见的,洗衣、淘米、坐船都靠它;江上船更是常见,运货、载人,谁家没个亲人坐过船?刘采春直接说“不喜”“生憎”,不绕弯子,老百姓一听就懂:“哦,这是恨水恨船把亲人带走了!”要是换个文人写,可能得说“秦淮淼淼送离舟,恨逐江波万里流”,美是美,可老百姓得琢磨半天“淼淼”是啥意思,“恨逐江波”又是啥感觉,哪还有心思共情?
还有“经岁又经年”这五个字,多实在啊!就是“一年又一年”,谁家等亲人不是这么熬过来的?卖布的王婶等儿子从扬州回来,等了“经岁又经年”;开茶馆的李嫂等丈夫从杭州回来,也是“经岁又经年”。刘采春不用“岁月如梭”“寒暑几易”,就用老百姓嘴边的话,一下子就把“等了好久”的感觉说透了。
她还特别爱写“细节小事”,这些事老百姓一看就眼熟。比如“金钗当卜钱”,金钗是姑娘家的宝贝,平时藏在首饰盒里,擦得锃亮,只有走亲戚、过节才戴。可思妇急着盼丈夫回来,连金钗都舍得拿出来当卜钱——扔一下,正面朝上就盼着“快回来了”,反面朝上就偷偷抹眼泪,再扔一次。这场景多真实啊!江南水乡的媳妇们,谁没为了盼亲人,干过点“傻事”?有的拿丈夫的旧帕子算命,有的对着月亮许愿,刘采春写的“金钗当卜钱”,就是把这些“傻事”唱出来了,老百姓能不觉得“这说的是我吗”?
有次刘采春在绍兴演出,台下有个穿粗布衣裳的媳妇,听她唱“金钗当卜钱”哭了。演出结束后,她拉着刘采春说:“姑娘,我前阵子也把我娘给我的金钗拿出来卜过,我家那口子去湖州做生意,半年没信了,我实在没办法,就想问问金钗,他啥时候能回来。”你看,刘采春写的不是虚构的故事,是老百姓的真实生活,所以才这么接地气。
对比一下当时的文人诗,更明白刘采春的“通俗”多可贵。比如有个叫李端的诗人,写思妇诗:
“月落星稀天欲明,孤灯未灭梦难成。”
写得也苦,可老百姓听了,顶多觉得“这姑娘睡不着”,却未必能想到自己——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“孤灯未灭”的闲情,更多人是累了一天,倒头就睡,梦里还在盼亲人。而刘采春写“朝朝江口望,错认几人船”,老百姓一听就懂:“是啊,我也天天去村口盼,看见像我家娃的身影,就赶紧跑过去,结果不是,心里空落落的。”
深情:不喊“我想你”,把眼泪藏在细节里
要是光通俗,没有深情,刘采春的词顶多是“顺口溜”,成不了能传千年的好作品。她的厉害之处在于:通俗的话里,藏着戳心窝子的深情,不喊“我想你”,不叫“我难过”,可每个字都在说“我想你”“我难过”。
最典型的是“朝朝江口望,错认几人船”。还原一下这个场景:天刚蒙蒙亮,江边还飘着雾,思妇裹着厚头巾,站在码头的石头上,脚都冻麻了,可眼睛一刻也不敢离开江面。远处来了一艘船,船帆上隐约有个“扬”字(扬州的简称),她心里一紧,赶紧踮起脚,手搭在额头上往前看——“是不是他的船?是不是他回来了?”船越来越近,她能看见船工的身影了,仔细一看,不是她丈夫,她的肩膀一下子垮下来,叹了口气,把手放下来,搓了搓冻红的脸,等着下一艘船。
就这么个场景,刘采春没写“我天天等,我好难过”,写“朝朝望”“错认船”,谁看不出她的难过?谁看不出她的思念?这种“不说情,却满是情”的写法,比喊一百句“我想你”都管用。有次刘采春在杭州演出,唱到这句时,特意放慢了语速,眼神里带着失落,手还轻轻往前伸了一下,又收回来——台下的观众,尤其是那些等亲人的媳妇,一下子就哭了,因为她们太懂这种“盼了又盼,空欢喜一场”的滋味。
还有“昨日胜今日,今年老去年”,这句更扎心。思妇看着镜子里的自己,昨天的皮肤还比今天好一点,今年的头发比去年白了不少——她不是在感叹“我老了”,是在怕“我等他回来的时候,我老得他不认得了”,是在怕“他回来的时候,我已经等不动了”。这种藏在“变老”里的焦虑,没有经历过“长期等待”的人,根本懂不了;可经历过的人,一听就会掉眼泪。
刘采春的深情,还藏在“理解”里——她不只是写思妇的苦,还写思妇的“懂”。比如“闻君欲下峡,定是逐梁州”,丈夫要去三峡,要去梁州,她没抱怨“你怎么又走了”,只说“定是逐梁州”——她懂丈夫是为了生意,是为了这个家,所以她不抱怨,默默记着他去的地方,盼着他平安。这种“懂”,比抱怨更让人疼——你想啊,一个女人,明明很想丈夫留下来,却因为懂他,只能把委屈咽下去,继续等,这种深情,多真实啊!
有个在苏州经商的男人,听了刘采春的《啰唝曲》,特意找到她,说:“姑娘,你唱的‘闻君欲下峡’,让我想起我媳妇。我每次跟她说要去外地,她都不说啥,只帮我收拾行李,可我知道她心里不好受。以前我总觉得我是为了家,没什么愧疚的,听了你唱的,我才知道她有多难。”你看,刘采春的深情,不仅能让女人共情,还能让男人理解女人的苦,这就是她的本事。
(本章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)第159章刘采春的艺术:大白话藏着真眼泪(第2/2页)
表演:用嗓子和动作,让深情“活”起来
刘采春不只是个“词人”,她还是个“表演者”——她的词,得唱出来,得演出来,才能把深情传到位。光看文字,可能还差点意思;一旦她站在戏台上,开口一唱,动手一演,那情感就像江水一样,直接流进观众心里。
先说说她的嗓子。她的嗓子不是那种尖细的,是婉转的,像江南的流水,能柔能刚。唱“不喜秦淮水,生憎江上船”时,她的嗓子里带着点怨气,咬字重一点,比如“不喜”“生憎”,能让人听出她的恨;唱“朝朝江口望,错认几人船”时,她的嗓子会变软,语速放慢,尤其是唱“错认几人船”时,会轻轻叹口气,让人听出她的失落;唱“金钗当卜钱”时,她的嗓子里带着点委屈,像在跟人诉苦,让人听了心疼。
有次刘采春在南京演出,唱到“金钗当卜钱”时,特意把声音压得很低,像在跟身边人说悄悄话,台下的观众都屏住呼吸,生怕漏了一个字。唱完这句,她还停顿了一下,眼睛里好像有泪光,台下的一个老妇人当场就哭了,说:“我年轻时也这么干过,我家老头子去当兵,我把我娘给我的银镯子拿出来卜,现在镯子还在,可他没回来。”
再说说她的表演动作。她不喜欢花里胡哨的动作,只做最贴合词意的动作,简单却传神。唱“朝朝江口望”时,她会把手搭在额头上,身体微微前倾,眼睛望向远方,像真的在看江面上的船;唱“错认几人船”时,她会先眼睛一亮,手往前伸一下,然后又慢慢收回手,肩膀垮下来,脸上露出失落的表情;唱“金钗当卜钱”时,她会假装从头上拔下金钗(其实是道具),用手指捏着,轻轻扔一下,然后低头看,脸上露出紧张的表情,像在等结果。
这些动作虽然简单,特别能带动观众。有次刘采春在扬州演出,台下有个小姑娘,跟着她的动作学——刘采春把手搭在额头上,她也搭;刘采春收回手,她也收回;刘采春露出失落的表情,她也跟着皱眉头。演出结束后,小姑娘拉着她娘说:“娘,这个阿姨好可怜,她等的人总不回来。”你看,连小孩子都能通过她的动作,感受到词里的情感,这就是表演的力量。
刘采春还特别会跟观众互动。她在台上唱的时候,会时不时看台下的观众,跟他们点头,像在跟老朋友聊天。有次她唱到“莫作商人妇”,台下有个媳妇大声说:“姑娘,你说得对!我就是商人妇,太苦了!”刘采春听见了,笑着对她说:“大姐,苦就跟我们说说,别憋在心里。”然后接着唱,台下的观众都觉得特别亲切,像在跟自己家姐妹聊天。
这种“唱+演+互动”的方式,让她的词不再是纸上的文字,而是活灵活现的故事。观众不是在“听戏”,是在“看自己的生活”——看那个在江边等船的自己,看那个拿金钗卜卦的自己,看那个盼亲人回来的自己。所以,刘采春的戏,能让卖菜的大妈放下秤,能让织布的姑娘停下梭子,能让赶路的商人停下来——因为大家都在她的戏里,看到了自己。
为啥她能把“通俗”和“深情”捏到一起?因为她懂老百姓
刘采春能做到“通俗与深情的完美结合”,根本原因是她“懂老百姓”——她不是高高在上的文人,她是跑江湖的民间艺人,她跟老百姓一起吃饭、一起聊天,她知道老百姓喜欢听啥、能懂啥、会为啥哭。
她跟着戏班跑江湖,每到一个地方,都会跟当地的老百姓聊天——跟洗衣的大妈聊“你家儿子啥时候回来”,跟织布的姑娘聊“你对象在哪儿经商”,跟开茶馆的大叔聊“最近有没有见过从外地来的船”。这些聊天的内容,都成了她词里的素材。比如“桐庐人不见,今得广州书”,就是她听一个媳妇说“我丈夫走的时候说去桐庐,结果现在从广州寄信回来”,然后写进词里的。
她也经历过老百姓的苦——戏班赶路时,遇上刮风下雨,驴车陷在泥里,一家人得下来推;演出时,戏台漏雨,她顶着雨唱,嗓子唱哑了也不敢停,因为要靠演出挣饭钱。这些苦,让她更能理解老百姓的不容易,更能懂那些思妇的委屈——所以她写的深情,不是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,是真真切切的“我懂你”。
有次一个文人问刘采春:“你写的词为啥这么通俗,却又这么动人?”刘采春笑着说:“我没读过多少书,不会写那些文绉绉的话。我知道,老百姓喜欢听实在话,喜欢看实在事。我把我看见的、听见的、懂的,唱给他们听,他们觉得‘这说的是我’,自然就会喜欢。”
艺术的最高境界,不是“阳春白雪”,不是让少数人称赞,而是“下里巴人”,让大多数人能懂、能共情。刘采春做到了——她用老百姓的话,讲老百姓的事,带老百姓的情,让通俗的词里藏着真眼泪,让简单的表演里满是真感情。
直到现在读《啰唝曲》,还能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和深情——“不喜秦淮水”的恨,“金钗当卜钱”的盼,“错认几人船”的失落,这些情感,跨越了千年,还是能打动我们。因为不管时代怎么变,“等待”的苦、“思念”的甜、“理解”的暖,都是老百姓共通的情感。
刘采春或许不是唐代最有名的诗人,她绝对是唐代最懂老百姓的艺人。她用自己的艺术,给了老百姓一个“说话的机会”,让那些藏在市井烟火里的深情,被看见、被听见、被记住——这就是她的艺术最珍贵的地方,也是她能成为中唐“流行天后”的真正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