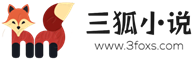第九十八章王建:从穷小子到“张王乐府”,
一秒记住【三狐小说】 www.3foxs.com,更新快,无弹窗!
第九十八章王建:从穷小子到“张王乐府”,(第1/2页)
安史之乱后的颍川(今河南许昌),到处是断墙残垣。有户姓王的人家,住在城郊的破屋里,屋顶漏雨,墙根透风,家里连块完整的门板都没有。
每到傍晚,就会有个半大孩子,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,就着邻居家透过来的油灯光,捧着本卷边的《诗经》啃——这孩子就是王建,后来和张籍并称“张王乐府”的诗人。那会儿没人知道他是谁,只知道是王家那个“爱读书的穷小子”。
颍川寒门:啃冷馍、借灯读,穷日子里长出的文学苗子
王建的苦,是打娘胎里带出来的。他出身“寒门庶族”,搁现在说就是“没背景的普通人家”,赶上安史之乱,家里的薄田被战火毁了,父亲早逝,母亲一个人拉扯他,日子过得“吃了上顿没下顿”。
小时候的王建,最盼的不是过年,是邻居家办丧事——不是心狠,是办丧事会煮大锅饭,偶尔能蹭上半碗粥;最宝贝的东西,是一本借来的《诗经》,封面掉了,书页缺了角,他用麻线缝了又缝,走到哪带到哪。有次母亲病了,没钱抓药,他想把书卖了,抱着书在集市上蹲了半天,最后还是没舍得——那是他唯一能看到“外面世界”的窗口。
他读书全靠“偷学”。村里有个老秀才,偶尔会教几个富家子弟读书,王建就趴在人家院墙外听,下雨了就躲在屋檐下,耳朵贴在墙上,生怕漏了一个字。老秀才见他可怜,又肯学,就偶尔把他叫进院里,教他认几个字,送他几张旧纸。王建把纸裁成小条,用炭灰兑水当墨,在上面练字,写满了就擦掉再写,一张纸能反复用十几次。
十几岁时,王建的诗就有点模样了。不是写风花雪月,是写身边的苦日子:邻居家的大婶因为交不起税,被差役拉走;村口的老王头,儿子死在战场上,连尸骨都没找回来。他写“桑柘废来犹纳税,田园荒后尚徵苗”,不是凭空想象,是天天看在眼里的真事。
母亲劝他:“读这些有啥用?不如学门手艺糊口。”王建没说话,把写满诗的纸,藏在枕头底下——他知道,对他这样的穷小子来说,读书写诗,是唯一能跳出寒门的路。
转机出在他十七八岁那年。他听说邻县有个学馆,管饭还不收学费,就揣着母亲连夜缝的粗布衣裳,走了三天路,找到了学馆。在这里,他遇上了这辈子最重要的朋友——张籍。
张籍比他大几岁,也是个穷书生,俩人一见如故。学馆的饭是稀粥配冷馍,菜只有腌萝卜,冬天冷得没法握笔,他们就挤在一张床上,裹着两床打补丁的被子,你念一句诗,我接一句评;没钱买纸,就一起捡别人扔的废纸,裁开了分着用;有次王建得了风寒,发烧咳嗽,张籍就半夜起来,帮他煎药,还把自己仅有的一件厚棉袄盖在他身上。
那段日子苦得掉渣,却成了王建一辈子的念想。后来他写过一首《寄张籍》,里面说
“忆昔君初纳彩时,不言身属辽阳戍。
早知今日当别离,成君家计良为谁?”
字里行间全是当年一起啃冷馍、共患难的热乎劲儿。也就是在学馆里,王建真正开始“写诗”——不再是随手记身边事,而是学着用更凝练的语言,把寒门子弟的挣扎、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写出来。
他写《村居即事》:
“休看小字大书名,向日持经眼却明。
时过无心求富贵,身闲不梦见公卿。”
表面是说“我不稀罕富贵,也不想当大官”,其实是穷书生的无奈与自我慰藉——不是不想,是知道太难,不如先守着眼前的平静。谁也没想到,这首诗里的“淡泊”,没几年就被现实打破了——为了活下去,他不得不踏上一条更苦的路:从军。
边塞十三年:从颍川书生到军营幕僚,刀光剑影里写出的“士兵悲歌”
贞元十三年(797),王建二十岁。这年河南大旱,学馆断了粮,他不得不回家。看着母亲饿瘦的脸,看着家里空荡荡的米缸,他咬了咬牙——科举遥遥无期,种地养不活家,不如去从军。那会儿幽州节度使刘济在招幕僚,听说只要有点文化,就能混口饭吃,还能有点俸禄寄回家。
王建跟母亲辞行那天,天还没亮。母亲把家里仅有的一块腊肉,切成小块包好,塞到他怀里,哭着说:“到了那边,别逞强,活着回来就好。”王建没敢回头,怕母亲看见他的眼泪,一路向北,走了一个多月,终于到了幽州。
幽州的冬天,比颍川冷十倍。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,吹得人睁不开眼,军营里的帐篷漏风,夜里冻得人直打哆嗦。王建是个书生,没学过打仗,只能做幕僚,帮着写文书、记军功。可就算是文书,也得跟着军队跑——今天扎营在山谷,明天转移到河边,有时候刚写完一份报告,敌军的箭就飞进了帐篷。
第一次见打仗,王建吓傻了。那天他跟着军队在边境巡逻,遇上敌军突袭,箭如雨下,士兵们惨叫着倒下,鲜血染红了雪地。
他躲在石头后面,浑身发抖,手里的笔都掉在了地上。晚上整理阵亡士兵名单时,他看着那些年轻的名字,想起离家时母亲的眼泪,突然明白:诗里写的“战争苦”,远不如眼前的刀光剑影来得真实。
从那以后,王建的笔变了。他不再写田园的平静,开始写边塞的残酷、士兵的痛苦。他的边塞诗,没有“大漠孤烟直”的豪情,只有“白骨露于野”的悲凉——因为他见过,所以写得扎心。
他写《渡辽水》:
“渡辽水,此去咸阳五千里。
来时父母知隔生,重著衣裳如送死。
亦有白骨归咸阳,营家各与题本乡。
身在应无回渡日,驻马相看辽水傍。”
想想那个场景:士兵们渡辽水去打仗,离家五千里,出发时父母就知道,这一去可能就是永别,所以给孩子多穿几件衣裳,像办丧事一样送他走;就算有幸把尸骨运回去,也是在墓碑上写个家乡的名字;更多的人,站在辽水边,望着家乡的方向,再也回不去。王建写这首诗时,手里握着的,可能就是某个阵亡士兵的家书——那些没寄出去的信,字里行间全是对家人的牵挂。
他还写《凉州行》,骂边将的荒淫:
“凉州四边沙皓皓,汉家无人开旧道。
边头州县尽胡兵,将军别筑防秋城。
……驱我边人胡中去,散放牛羊食禾黍。去年中国养子孙,今著毡裘学胡语。”边将们只顾着自己享乐,不修边防,让胡兵占领了州县,还把老百姓赶到胡地,让他们学着说胡语、穿胡服。王建在诗里没喊“边将无能”,却用“去年养子孙,今著毡裘”的对比,把边将的罪责骂得明明白白。
(本章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)第九十八章王建:从穷小子到“张王乐府”,(第2/2页)
在幽州的十三年,王建从一个二十岁的书生,变成了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。他的脸被风沙吹得粗糙,手因为常年握笔、写文书,磨出了厚茧,眼睛里也没了早年的青涩,多了几分沧桑。他寄回家的俸禄,让母亲的日子好过了些,可他自己,却常常在夜里失眠——他见过太多死亡,太多分离,太多苦难,这些都像石头一样压在他心里,只能靠写诗来排解。
有次他跟着军队到了一个叫“蓟门”的地方,夜里睡不着,走出帐篷,看到月亮挂在天上,照在荒凉的边塞,突然想起了远在颍川的母亲,想起了学馆里的张籍。他掏出纸笔,借着月光写了首《蓟门行》:
“蓟门逢古老,独立思氛氲。
一身既零丁,头鬓白纷纷。
勋庸今已矣,不识霍将军。”
他觉得像个“古老”,在边塞待了这么久,功业没成,头发却白了,连当年崇拜的霍将军,也觉得遥远。
可也就是这十三年的边塞生活,把王建“磨”成了真正的诗人。他不再是那个只能写身边小事的寒门书生,而是能看透社会现实、为底层人说话的“写实诗人”。他见过士兵的苦,后来就能写百姓的苦;他见过边将的贪,后来就能写官吏的恶。这些经历,成了他后来创作“乐府诗”的家底——那些从刀光剑影里长出来的诗,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有力量。
贞元末年,刘济去世,幽州军镇大乱。王建看着军营里的厮杀,看着曾经一起共事的人互相残杀,觉得累了。他收拾好诗稿,辞了官,一路向南,回了颍川。
走的时候,他没带多少东西,只有一箱子写满诗的纸,还有一件张籍当年送他的厚棉袄——那件衣服,他穿了十三年,补丁摞着补丁,却一直没舍得扔。
回到颍川的那天,母亲拄着拐杖,在村口等他。看到他回来,母亲哭着摸他的脸:“瘦了,黑了,可总算回来了。”王建抱着母亲,也哭了——十三年的边塞生涯,他没掉过几次眼泪,可在母亲面前,所有的坚强都崩了。
那天晚上,母亲做了他最爱吃的面条,放了点腊肉。王建一边吃,一边跟母亲说边塞的事,说他写的诗。母亲听不懂诗里的大道理,却笑着说:“能平安回来就好,能写诗就好。”王建看着母亲的笑脸,突然觉得,十三年的苦,值了——他不仅活着回来了,还把那些苦难,写成了能留下来的诗。
诗里的“人间烟火”:从边塞到市井,他的笔始终对着底层人
回到颍川后,王建歇了一段时间,又开始四处奔波——他还是想考科举,想当一个能为百姓做事的官。可科举之路对他这样的寒门子弟来说,依旧难走。他考了几次,都没中,直到四十多岁,才终于考中了进士,当了个小官。
可当官后的王建,没变。他没像别的官员那样摆架子,反而更关注底层人的生活。他的诗,也从边塞转向了市井,写卖炭的老人、织锦的农妇、守边疆的士兵,写他们的苦、他们的难、他们的希望。
他写《田家行》:
“男声欣欣女颜悦,人家不怨言语别。
五月虽热麦风清,檐头索索缲车鸣。
野蚕作茧人不取,叶间扑扑秋蛾生。
麦收上场绢在轴,的知输得官家足。
不望入口复上身,且免向城卖黄犊。
田家衣食无厚薄,不见县门身即乐。”
农民们五月忙着收麦、缫丝,看似“欣欣悦悦”,其实是怕交不够赋税,盼着“免向城卖黄犊”,能保住家里的牛就好。王建写的不是“农家乐”,是农民“敢怒不敢言”的无奈——不用去县衙交税,就是最大的快乐。
他还写《织锦曲》:
“大女身为织锦户,名在县家供进簿。
长头起样呈作官,闻道官家中苦难。
回花侧叶与人别,唯恐秋天丝线干。
红缕葳蕤紫茸软,蝶飞参差花宛转。
一梭声尽重一梭,玉腕不停罗袖卷。
窗中夜久睡髻偏,横钗欲堕垂著肩。
合衣卧时参没后,停灯起在鸡鸣前。
一匹千金亦不卖,限日未成宫里怪。
锦江水涸贡转多,宫中尽著单丝罗。
莫言山积无尽日,百尺高楼一曲歌。”
织锦的女子,没日没夜地织锦,织好的锦“一匹千金不卖”,全要交给宫里,宫里还嫌不够,就算锦江水干了,还要多要。王建写的是织锦女的辛劳,也是对宫廷奢侈的无声批判。
这些诗,后来被人称为“乐府诗”,他和张籍的乐府诗,因为风格相近、都写写实,被并称“张王乐府”。有人说,王建的乐府诗“字字见血,句句见泪”,他却说:“我把看到的写下来而已。”他没忘记是寒门出身,没忘记边塞的苦,所以他的笔,始终对着那些像他早年一样挣扎的底层人。
晚年的王建,官越做越大,当了陕州司马、光州刺史,可他还是老样子——穿粗布衣裳,吃简单的饭,没事就写诗。他跟张籍还经常通信,互相寄诗,点评对方的作品。张籍写“家贫无易事,身病足闲时”,王建就回“自别青山归未得,羡君长听石门泉”,俩人还是当年学馆里的样子,头发都白了。
约830年,王建在任上去世,享年六十多岁。他去世后,家人整理他的遗物,发现除了一箱子诗稿,没什么值钱的东西——他当了一辈子官,没贪过一分钱,没置过一亩田,把所有的心思,都放在了写诗上。
后来有人把他的诗编成了《王司马集》,流传到现在。翻开这本书,你看不到“大诗人”的架子,只能看到一个从颍川寒门走出来的穷小子,一个在边塞摸爬滚打十三年的士兵,一个为底层人说话的官员——他把自己的苦难、别人的苦难,都写成了诗,没有华丽的辞藻,没有空洞的道理,只有最真实的人间烟火。
现在再读王建的诗,还是会被戳中——读《渡辽水》,会心疼那些再也回不了家的士兵;读《田家行》,会想起那些在田里辛苦劳作的农民;读《寄张籍》,会想起年轻时一起共患难的朋友。这就是王建的厉害——他写的不是“诗”,是“人”,是每个在苦难里挣扎,却依然想好好活下去的人。
他的人生,就像他写的诗一样,平凡却有力量。从颍川的穷小子,到边塞的幕僚,再到“张王乐府”的诗人,他没走什么捷径,一步一步,把苦难踩在脚下,把生活写进诗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