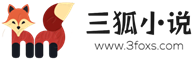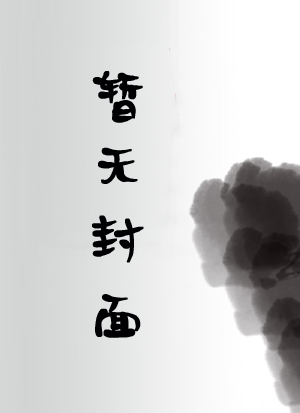第九十七章 张籍与白居易、元稹 共赴中唐之约
一秒记住【三狐小说】 www.3foxs.com,更新快,无弹窗!
第九十七章张籍与白居易、元稹共赴中唐之约(第1/2页)
张籍与白居易、元稹的交往,从来不是文人间虚浮的应酬,而是以乐府诗为纽带、以民生关怀为底色的同道之谊。三人同为中唐“新乐府运动”的核心推动者,都主张“诗言志、为民声”,这份对诗歌理想的共识,让他们从文字知己,成了彼此人生里的“诗友脊梁”。
张籍与白居易:从“诗坛互赏”到“洛阳忘年”
白居易比张籍小4岁,却更早以《秦中吟》崭露头角,但他对张籍的乐府诗,始终带着“晚辈对前辈的推崇”。早在长安时期,白居易就读过张籍的《野老歌》《征妇怨》,读完直言“尤工乐府诗,举代少其伦”——这话不是客套,是他在《与元九书》里特意写的,等于公开把张籍抬到了“中唐乐府第一梯队”的位置。
张籍也懂白居易的“诗心”。白居易写《卖炭翁》揭露宫市之苦,张籍就写《贾客乐》批判商人盘剥;白居易用“老嫗能解”的通俗语言写诗,张籍也坚持“不雕饰、说真话”,两人就像“诗坛双子星”,你写一段百姓苦,我续一篇人间难,彼此呼应。
后来两人都退居洛阳,交往更密。白居易在自家“履道里宅”设酒局,必请张籍;张籍住的茅屋离得不远,常拄着拐杖就去了。有回白居易病了,张籍特意写《赠白居易》,诗里没说虚话,写“病来容貌减,老去友朋疏。唯有张居士,见予还下车”,把晚年相惜的情谊写得朴素又暖。白居易读了当即回诗《答张籍因以代书》,说“君年虽少我,白发已先我。我昔少年时,亦曾如此作”,像老友聊天似的,道尽岁月里的知己情。
他们的交往里,没有官位高低的计较,只有“你懂我的诗,我知你的苦”——白居易叹“官闲似致仕,年长如退休”,张籍就陪他“共赏洛阳秋,同吟渭水愁”,把晚年的清贫日子,过成了诗里的“岁月静好”。
张籍与元稹:从“文字共鸣”到“患难相扶”
元稹比张籍小7岁,就把张籍当“诗坛前辈”敬着。他编《元氏长庆集》时,特意收录了张籍的20多首乐府诗,还在序言里写“张籍乐府,其意切而词质”,等于帮张籍的诗扩大了影响力。
两人的交情,最动人的是“患难里的诗信”。元稹被贬通州时,又病又愁,写了首《病卧闻幕中诸公征乐会饮因有戏赠》,满纸都是“孤独”,寄给了长安的张籍。张籍读了立刻回诗《寄元员外》,没说“加油”“挺住”的空话,只写“通州君初到,郁郁愁如结。江州我方去,迢迢行未歇”——我知道你贬谪的苦,因为我也曾走在贬官的路上,这份“同病相怜”,比任何安慰都管用。
(本章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)第九十七章张籍与白居易、元稹共赴中唐之约(第2/2页)
后来元稹回长安当宰相,也没忘了张籍。当时张籍官小,还常受排挤,元稹就多次向朝廷举荐,说“张籍有大才,能为百姓立言”。有人劝元稹“张籍性子直,不会站队,你举荐他没用”,元稹却笑说“我荐的是他的诗,是他的心,不是他的‘站队’”。
张籍也记着这份情。元稹后来又被贬武昌,病得重,张籍特意托人寄去熬的药,附诗《酬元员外》,写“昔岁俱为江外客,今年同到洛阳城。且喜筋骸俱健在,莫嫌须鬓各皤然”——咱俩从江南贬谪到洛阳相聚,如今你又遭难,只要身子还在,就有再聊诗的日子。可惜这首诗寄到武昌时,元稹已经去世,张籍听说后,对着诗稿哭了半天,把诗烧给了元稹。
三人的“共同底色”:诗为民生,不为虚名
张籍、白居易、元稹的交往,从来不是“诗酒唱和的热闹”,而是“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”的理想契合。他们都反感“为诗而诗”的风花雪月,都坚持把“老农的饥寒、征妇的眼泪、士兵的劳苦”写进诗里——
-白居易写“卖炭翁,伐薪烧炭南山中”,张籍就写“老农家贫在山住,耕种山田三四亩”;
-元稹写“昔日戏言身后意,今朝都到眼前来”(悼亡),张籍就写“十载来夫家,闺门无瑕疵”(叹弃妇);
-三人聚会时,聊的不是官场八卦,而是“最近又听百姓说什么苦,该写首诗记下来”。
这种“以诗为器,为民生发声”的共同追求,让他们的交往超越了普通朋友,成了“精神上的战友”。就像白居易说的“吾与元九、张十八,同志为文,共挽中唐之颓风”——他们要挽的,不只是诗坛的颓风,更是对百姓疾苦的“漠视之风”。